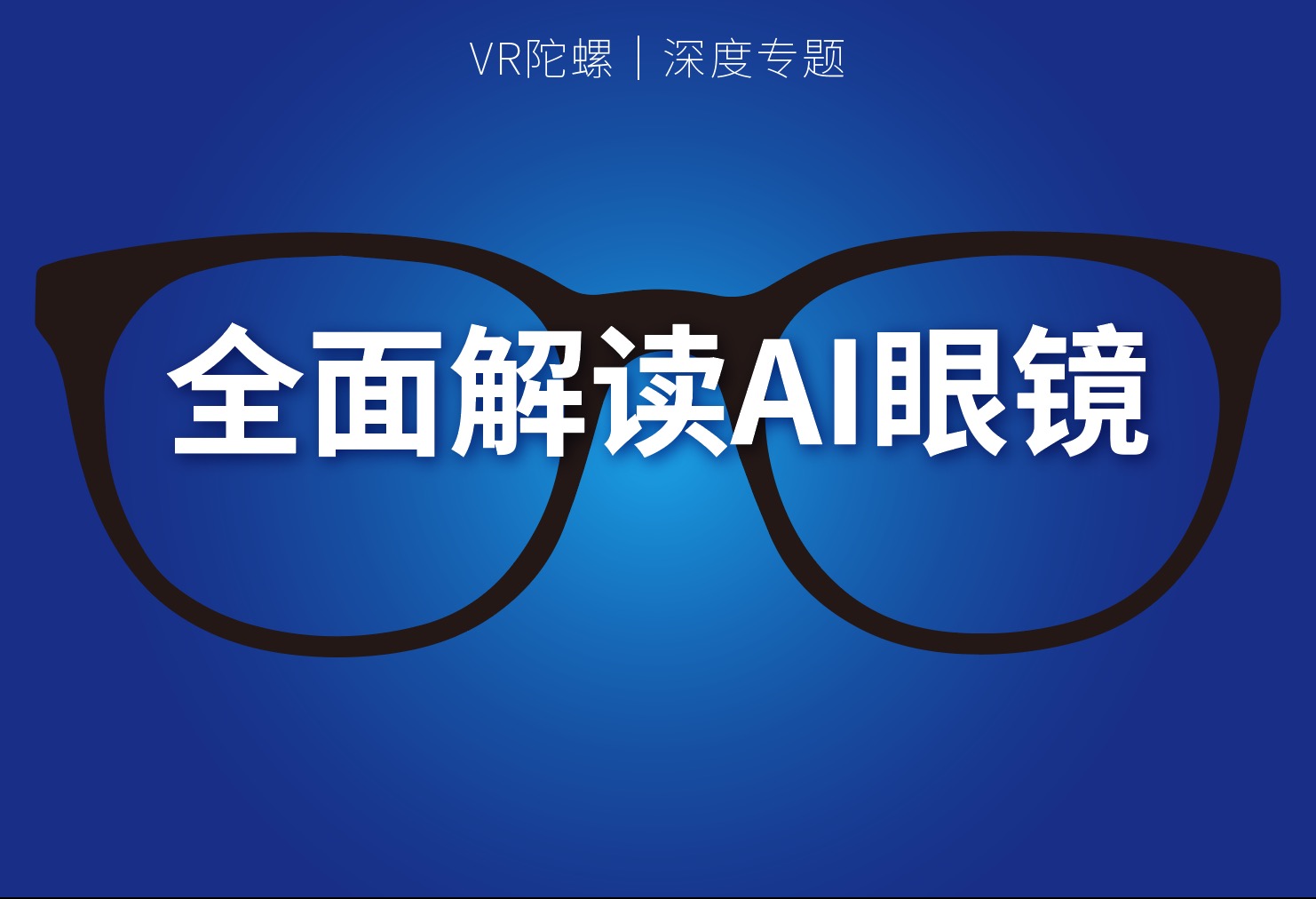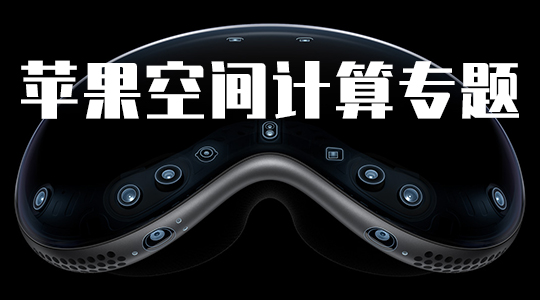去年,由于两个硬件上的突破,人们对VR产业的兴趣大增。一个是Oculus Rift,这款售价高达600美元的产品用极佳的视场角和音效让用户沉浸其中。另一个产品是谷歌的Cardboard,售价仅15美元的手机盒子。这两款产品都运用了陀螺仪和传感器来使用户的头部和画面同步运动。相比Oculus Rift的黑科技,Cardboard更像是19世纪的透视镜:两块镜片设定至合适的角度来产生画面具有深度的错觉。
这些VR技术上的发展让一些博物馆开始寻找新的、更好的展示自己的方法。谷歌和许多博物馆都进行了合作,让观众可以体验分布在伦敦、布鲁塞尔、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的3D参观旅程。还有一些博物馆直接做出了VR app:位于华盛顿的Renwick画廊近日发布了馆内雕塑展览“Wonder”的VR版。但实际上这些VR体验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手机的分辨率太低,镜片所需的角度太过复杂,导致完全重现博物馆游览变得十分困难。再加上在观展过程中观众只能移动双眼而非双脚,让人感觉只是在看一个全景的展览馆图片。
相比之下,在展览本身使用VR则显得更加有趣,无论是作为教育工具还是独立的艺术品。位于纽约的犹太博物馆内正在展出法国建筑设计师皮埃尔·查里奥(Pierre Chareau)的作品回顾展,其中就用到了VR技术将观众传送至查里奥一处位于巴黎的建筑作品内。此时你只用戴上VR眼镜,建筑内的装潢设计就会完整的呈现在眼前。
艺术家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将VR作为一种媒介使用在作品中。美国艺术家Ian Cheng在2013年时就采用了Oculus Rift原型机来呈现自己的动态视觉艺术。到了2015年时,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三年展上,西班牙艺术家Daniel Steegmann Mangrané用Oculus Rift将观众传送到巴西的热带雨林里,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飒飒作响的树叶和草丛,现实中却像一个傻瓜般在展览馆内手舞足蹈。在即将于今年3月17日开始的惠特尼双年展中,也有多个由先锋艺术家们发起的VR艺术项目。
去年,由于两个硬件上的突破,人们对VR产业的兴趣大增。一个是Oculus Rift,这款售价高达600美元的产品用极佳的视场角和音效让用户沉浸其中。另一个产品是谷歌的Cardboard,售价仅15美元的手机盒子。这两款产品都运用了陀螺仪和传感器来使用户的头部和画面同步运动。相比Oculus Rift的黑科技,Cardboard更像是19世纪的透视镜:两块镜片设定至合适的角度来产生画面具有深度的错觉。
这些VR技术上的发展让一些博物馆开始寻找新的、更好的展示自己的方法。谷歌和许多博物馆都进行了合作,让观众可以体验分布在伦敦、布鲁塞尔、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的3D参观旅程。还有一些博物馆直接做出了VR app:位于华盛顿的Renwick画廊近日发布了馆内雕塑展览“Wonder”的VR版。但实际上这些VR体验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手机的分辨率太低,镜片所需的角度太过复杂,导致完全重现博物馆游览变得十分困难。再加上在观展过程中观众只能移动双眼而非双脚,让人感觉只是在看一个全景的展览馆图片。
相比之下,在展览本身使用VR则显得更加有趣,无论是作为教育工具还是独立的艺术品。位于纽约的犹太博物馆内正在展出法国建筑设计师皮埃尔·查里奥(Pierre Chareau)的作品回顾展,其中就用到了VR技术将观众传送至查里奥一处位于巴黎的建筑作品内。此时你只用戴上VR眼镜,建筑内的装潢设计就会完整的呈现在眼前。
艺术家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将VR作为一种媒介使用在作品中。美国艺术家Ian Cheng在2013年时就采用了Oculus Rift原型机来呈现自己的动态视觉艺术。到了2015年时,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三年展上,西班牙艺术家Daniel Steegmann Mangrané用Oculus Rift将观众传送到巴西的热带雨林里,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飒飒作响的树叶和草丛,现实中却像一个傻瓜般在展览馆内手舞足蹈。在即将于今年3月17日开始的惠特尼双年展中,也有多个由先锋艺术家们发起的VR艺术项目。

Ian Cheng 展品
现在VR艺术甚至走出了博物馆本身,来到了观众的手机上。上个月,观众可以在手机上免费观看纽约新博物馆的一个数字艺术展览。在这个名为“第一印象:艺术家们的VR”的展览中,展品大都采用了制作成本较低的VR动画,且充满了超现实元素:物体在空间中漂浮,不同的空间坍塌、融合在一起。与VR游戏不同,这些艺术作品并不会和观众有交互,而大多是对VR这种新媒体的实验性探索。这些视频的时间并不长,但体积仍然很大,因此观众需要确保手机留有足够的空间。 这个展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来自Rachel Rossin,一个游走于绘画和VR之间的年轻艺术家。她的作品《人类面具》(Man Mask)让观众置身一个模糊、纯白的世界,就像是在游戏《使命召唤》中一样。Rachel在这个世界中将游戏里士兵的形象扭曲成半透明的影子,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念咒般的不停在重复说着“幸福、和平和快乐”。
《Man Mask》
展览中的作品题材涉猎很广。纽约艺术家Jayson Musson创作了一首伤感的挽歌,献给所有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观众可以在VR中看到夜晚的满天星星,每一颗星星旁边都有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另一位艺术家Jeremy Couillard的作品中呈现了一个人类死后的世界,观众会看到自己的灵魂从一具尸体上升起,从一个五彩斑斓的管子中飘走。 许多艺术家在运用到VR时更像是游戏设计师或电影动画师,而非画家或者雕塑家。结果就是,只有极少数作品会运用到沉浸感的功效。所有在“第一印象”中的VR作品都可以3D的形式呈现,观众可以不戴VR眼镜直接在手机上观看,并且没有太大区别。 还有一些作品,如Jacolby Satterwhite的《Domestika》,甚至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观看效果更好,因为其本身与2D视频也没有太大区别。尽管VR图像是以球形而非平面渲染而成,但在效果区别不大的情况下,观众又何必带着一个碍事的VR眼镜在头上呢?
《Domestika》
新兴技术在过去已经数次想要彻底改变传统艺术的形式,但这种信誓旦旦的革命却迟迟没有到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网络艺术”的繁荣,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破裂这种艺术形式也渐渐被遗忘。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在去年夏天进行了中国艺术家曹斐的同名个展“Cao Fei”。在展览中,一台不联网的电脑播放着她的虚拟电影《第二人生》。在这个和200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脑游戏同名的电影中,曹斐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环境,主人公“中国Tracy”就生活在其中。
《第二人生》
相比VR,AR技术在艺术中的应用似乎更加广泛。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在去年夏天任命艺术家Tamiko Thiel创作一件AR艺术作品,游客可以在公园的绿道上看见虚拟的草地和鲜花。但就实际效果来看,尽管谷歌眼镜有望“变革艺术博物馆”,但AR现阶段还是会为许多人带来混乱的感觉。
Tamiko Thiel作品
VR对于许多游戏设计师来说也许行得通,但是在美术和艺术中的应用度却有所下降。这些艺术家所呈现的图像应当拥有更加广阔的深意,而非简单的展示。这也是当代艺术教给我们的宝贵一课:艺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幻象。当人们将媒介的能力推到极限时,艺术就会获得更深层次的意义。VR正好相反,它是没有边界的,因为这种媒介几乎能创造出和我们的真实生活中一模一样的世界。当我第一次戴上Oculus Rift并且来到艺术家们创作的热带雨林和漂浮世界中时,这种感觉是非常惊奇的。对于艺术家来说,当下的挑战在于如何能够运用VR来为更加复杂的艺术服务,因为惊奇感是远远不够的。 关注微信公众号:VR陀螺(vrtuoluo),定时推送,VR/AR行业干货分享、爆料揭秘、互动精彩多。 本文首发于纽约时报, 由VR陀螺编译。转载请注明来源。投稿/爆料:tougao@youxituoluo.com
稿件/商务合作: 六六(微信 13138755620)
加入行业交流群:六六(微信 13138755620)

元宇宙数字产业服务平台
下载「陀螺科技」APP,获取前沿深度元宇宙讯息